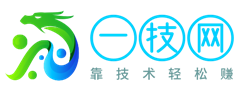《海洋奇緣2》海報:如同文身、巖畫一樣的海洋冒險歷程
在暌違8年之后,11月27日《海洋奇緣》IP迎來了全新冒險的第二部《海洋奇緣2》(Moana 2),并以席卷之勢風靡全球。《海洋奇緣2》首支預告片上線24小時就直接斬獲1.78億次播放,創下迪士尼旗下觀看次數最多的動畫預告片的全新記錄。在正式上映之后當日,它也成為迪士尼動畫影史單日票房第一名。并且直接將第47、48周全球各國電影票房冠軍納入囊中。根據2024年的票房數據,《海洋奇緣2》成功躋身2024年全球票房排名前四。
薩摩亞裔(Samoans)美國編劇達娜(Dana Ledoux Miller)加入到《海洋奇緣2》的導演工作,以原住民、少數族裔和女性視角重新擴展了這個來自南太平洋島嶼的海洋部落世界觀,讓這部動畫電影以一種洋溢著強烈樂觀的冒險精神,結合波利尼西亞(Polynesia)神話的現代化改編與大航海時代時的奇幻探索式英雄主義,將闊別已久的海洋歌劇(Ocean Opera)重新帶回到觀眾面前。
本片的核心故事改寫自半神毛伊(Māui)神話傳說中的“用神奇魚鉤釣起一座島”部分,這座島就是長白云之鄉,新西蘭的北島。迄今為止,北島的毛利名還是Te Ika a Maui(意為“毛伊的魚”)。而莫阿娜這一虛構角色,在大銀幕上以介入大眾文化的新時代公主形象(盡管她在電影中再三強調“我不是公主”),作為海洋文化表述的中繼站(Discursive Replay Station),用自身傳遞并重新改寫了這一神話故事的互文講述:這不再是半神毛伊用神力創造靜態歷史的獨幕劇,而是結合了部落記錄與冒險未知的動態事件,莫阿娜的遠航究其本質,不僅為了發現未來的可能性,同時也是為了找回丟失的過去,這不是通過懷舊的方式去喚醒記憶,而是通過創造新的“神話的永恒回歸”來完成探索。
在故事的最后,毛伊依然還是如神話講述那樣,釣起了象征“中心”的島嶼,但這早已與刻在毛伊身上的文身記憶大不相同,而是在修復性記憶(prosthetic memory)的增補下,經由電影這種記憶裝置變成了為莫阿娜重新加冕半神的儀式[1];同時《海洋奇緣2》的流行也為“當下社會提供了某種社會性整合和想象性救贖的力量”[2],那便是不再將視線停留在現實世界中爭奪存量,而是用重新記錄與啟航未知的范式去創造增量:自然/神話依然神秘,依然永遠值得我們去發現。這也是迪士尼一如既往在自己的影視作品中通過文化挪用的方式,進行一輪又一輪的擬像化文藝復興。
同樣是薩摩亞裔的巨石·強森(Dwayne Johnson)不僅繼續擔任半神毛伊的配音演員,并且也繼續獻唱歌曲。在本部電影中為《Can I Get A Chee Hoo?》(中文歌為《勇氣之歌》),那句“出發吧!遠航吧!將歷史改寫吧!”(You’re gonna,you’re gonna, a make some History)正是將“身體-文身-神話-歷史-互文”這一持續改造的模式演繹為文學繪圖。
《海洋奇緣2》:海報 布滿文身的半神毛伊
一、在身體上繪圖:文身上的銘記
在動畫的最后,經歷生死考驗的莫阿娜在族人的歌唱中重新復活。她與半神毛伊一樣,整個左手加手臂和前胸處出現了與“釣上的島嶼”高度相似的文身,這不僅意味著莫阿娜也成為了波利尼西亞海洋傳說中的半神,同時也呼應了現實世界中這一民族的文化歷史傳承:文身。
文身(Tattoo)的詞源來自塔希提島(Tahiti)上波利尼西亞語的“ta”和“tatatu”,前者意思是“印象深刻的”,后者則是“標記”,早在兩千余年前(可能就是莫阿娜生活的時期)波利尼西亞人就把自己的家族、歷史、個人經歷等諸多內容與圖案的方式永久地固定在自己的皮膚上。
正是因為在大航海時期,歐洲人對塔希提人的文身引發了強烈興趣。1768-1771年,到南太平洋考察的奮進號(HMS Endeavour)上,博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首次命名該詞,詹姆斯·庫克船長(Captain Cook)則將一位名叫馬依(Ma’i)的塔希提人帶回歐洲,這一在“身體上繪制圖案”的文化才在全世界流行起來。
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波利尼西亞民族就是最早掌握文學繪圖(literary cartography)的民族之一。
文學繪圖這一概念的系統化最早是由塔利(Robert Tally)建構并完善的,在《文學繪圖:敘事作為一種空間象征行為》(On Literary Cartography,2011)中給出了這個詞的完整定義:“文學作品通過創造寓言式的、象征性的社會空間表征來行使繪圖功能”,并在《空間性》(Spatiality,2013)里進一步闡釋“寫作行文本身或許可以被看作某種繪圖形式或制圖行為”,其內在驅動力就是繪圖緊迫性(cartographic imperative),即“主體每時每刻都想知道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就像有個始終都想確定觀光地圖上的‘你在這里’那個標志”[3]。
這正與莫阿娜在故鄉莫圖魯尼島(Motunui)與沉沒島莫圖斐度島(Motufetu)之間的徘徊相對應,但莫阿娜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她如果找不到被詛咒、被抹除、被遺忘的莫圖斐度島,她所在的莫圖努伊族(Motu Nui)就會面臨滅絕的危險,這是種族無法獲得聯系的,在“黑暗森林”中迷失的繪圖焦慮(cartographic anxiety),“此暗示抹殺了空間、地方和繪圖的歷史維度”[4]。
彼得·圖爾奇(Peter Turchi)認為,有兩種不同又重疊的完成文學繪圖的方式,分別是探索(exploration)與呈現(presentation),“探索被理解為有預謀的搜索和無紀律的、或許只是半意識漫步的組合,呈現是指有意創造一份旨在與他人溝通并對他人產生影響的文件”[5]。如果說莫阿娜帶領帆船發明家樂托(Loto)、故事記錄者莫尼(Moni)、老農民凱萊(Kele)等船員組建的團隊去尋找莫圖斐度的過程,是在沒有地圖,只有祖先的靈魂形象與形成的星辰——這又何嘗不是經典的文學繪圖方式,即線性透視(linear perspective)與數學投影(mathematical projection)——中是探索的話,那以文身形式將這段經歷附著在莫阿娜身上的標記就是呈現。
《海洋奇緣2》作為迪士尼100周年之后的首部動畫電影,開啟了對過往作品的文學再繪圖過程,2025年亦有多部續集作品和真人改編作品會上映,這可以被認為是對IP的再文身。身體的文學繪圖在迪士尼動畫中變得更加顯著,這是因為動畫制作過程中幾乎貫穿了“符號式身體/寫實性身體結合”的這一理念。
符號式的身體意味著角色可以在現實中看似難以實現的動作場景下自由穿梭,這也是半神毛伊在不同動物身體里不斷變形所形成的“卡通物理學”:
“在好萊塢喜劇和迪士尼動畫中常見的事實是,這些角色在身體上難以被殺死。即使米老鼠從懸崖上摔下來,被壓扁在地上,他也會毫發無損地出現在下一個場景中。這種迪士尼帶來的永恒或不死的身體是好萊塢動畫的遺產之一。毋庸置疑,這種不死的身體是以漫畫為基礎的繪畫表現形式的必然趨勢,同時,正如 Max Lüthi所討論的,童話具有類似的刀槍不入的身體性,這種風格被稱之為平面性。”[6]
而寫實性身體則是另一種更加帶來代入感的迪士尼特色。迪士尼動畫被保羅·威爾斯(Paul Wells)認為是“超級寫實主義”,作為“動畫片的強勢語言,借助動作層面的逼真性、合理性與可信度來追求真實”[7],并且采用對現實動物/人類的身體/動作摹仿達到逼真性,這是因為迪士尼動畫參考了很多在場的動作捕捉,將現場表演轉譯為數字表演,然后重新固定到動畫人物上,以形成一種更加真實的形象連續身體感。比如在設計莫阿娜這一形象時,制作方就將其設定為“有真實身材的女性”,并且視覺藝術Neysa Bové在服裝設計上嚴格遵照南太平洋當地文化[8]。
而當明星介入的時候,這份情感親和力變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巨石強森與半神毛伊之間的強親緣性。在上文中筆者談到《海洋奇緣》系列原本就是呈現強森所在的薩摩亞族的生活與神話,本作里半神毛伊所形成的動畫身體則對強森身體的互文性繪圖,它早已脫離原本的神話身體,變得更具有強森的明星特性(而非真實人物性):
“動畫制作者突出了他的胸和手臂,這是強森的人類身體中最壯碩的部分……毛伊復制了他的闊下巴……裝飾強森左肩的部落文身覆蓋了毛伊的全身,并且是其性格和故事的重要構成……在該片中是一個可能有點白癡的自吹自擂者,這種描寫恰好與道恩·強森有關,并且更像他的摔跤角色,巨石,一個傲慢或自戀的硬漢老爸角色。”[9]

《海洋奇緣2》海報:有各種文身的魚鉤與船槳
二、敘述下的活化:被改寫的記憶
在半神毛伊身上除了有巨石強森的明星特性以外,還記錄了毛伊過往的神話故事,甚至還有一個迷你毛伊,用以再現當年毛伊勾住太陽的壯舉,它的長相也更加符合波利尼西亞神話中對毛伊描述的模樣。
于是這層互文關系實現了倒置,講述者成為講述載體被記錄下的故事,而這正是莫圖魯尼島居民最缺少的東西,也是他們讓莫阿娜成為尋路者(wayfinding)的最重要原因——找回屬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記憶,哪怕是被迪士尼重新改寫之后的,被規訓為意識形態娛樂機器下的文化記憶。
在《海洋奇緣》第一部中,莫阿娜找回特菲堤之心(Heart of Te Fiti)重新拯救海洋,只是完成了神祗層面的歸位,但現世層面的敘事延續成為第二部亟待解決的問題。哪怕在第二部的開始,莫安娜在不同荒島上穿梭,用海螺呼喚其他族群的同伴,也依然杳無音信,最多只能聽到憨憨雞(HeiHei)的模仿。
這是因為古神納羅(Nalo)通過將莫圖斐度島沉入海底的方式徹底斬斷了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即通過“抹殺未來”完成了“消除過去”的回溯性探問(Rückfrage),讓海洋民族喪失了屬于自己的記憶,并沒收了可以記錄故事的文字。而這份“納羅抹殺過去”的過去也被抹除,變成遺忘者的遺忘。直到莫阿娜正式成為尋路者,才被自己的祖先陶泰·瓦薩(Tauti Vasa)以數學投影的方式再度活化,用可意象(imageable)的經歷彌補可知性(konwability)的匱乏,才得以將這段過去重新浮現出來。不過陶泰·瓦薩的出海經歷依然只是站在人類海洋敘事視角去探索的過程,勾勒出的是一份寓言式(allegorical)地圖,而非一份有著標記的波托蘭航海圖(portolan chart)。最后祖先只能化為星辰,作為帶領莫阿娜團隊成為朝向(orientation)重走歷程可能的方向性指引。
海洋族人最終通過“蘇醒/喚醒”這一行為的時間記憶隱喻,完成了逃離納羅阻斷記憶的神罰,就如(在第二部里已經變為刺鰩)的塔拉祖母(Rachel House)所說“我們沒有死亡,只是以另一種形式陪伴在身邊”。莫阿娜也經由代代傳承的尋路者的責任,以及壁畫上的民族代際故事獲得了這份來自過去的記憶,并經由兩種新的回憶形態從“公主敘事變為過往敘事”:
“一方面是歷史化的經驗——清醒、異化、孤僻,另一方面強調主觀上的重新定向——借助參與、直覺和幻想。過去已經死亡,但是某種天賦、某種創造性精神或許能夠令他復活。”[10]
納羅的神罰讓海洋民族對海洋的隱喻除了探險之外,還增加了迷失與拋離的意味,并形成“超驗的無家可歸”(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這在椰子海盜卡卡魔拉特(Kakamorat)上體現得更加明顯,并形成一種無法棲居狀態下的得以參照的地理批評(geocriticism):這些椰子海盜不能言說,不能記錄自己的歷史,被迫漂離在海洋上,需要用安康魚的毒液作為保護自身的武器,并承擔著致幻劑效果進而麻痹自己,這也是游蕩者(flâneur)的哲學宿命。
不過所幸的是,在《海洋奇緣2》中莫阿娜的隨行船員里有樂托、莫尼與凱萊,讓整個海洋冒險不再是可能被遺忘的過程,他們三人的功能正好成為拉康所談及的波羅米結(Borromean knot)的交織。莫阿娜與三人的互動最能體現彼此性情的,就是追尋祖先星辰痕跡過程中演唱的歌曲《最好的都在這里》(What Could Be Better Than This)。
經驗豐富的農民凱萊是實在界(the Real)的具象。真實的航海過程并不是文學繪圖,需要大量糧食才能保證旅途順暢。同時凱萊作為老年長輩,在這一代人的成長中,以肉身記憶見證莫圖魯尼島的日常。
擅長帆船設計的樂托是象征界(the Symbolic)的具象。航海歷程的實現需要“船”的實體化,這是一個被標記好的未來能指,也是實現尋找被詛咒島嶼這一欲望的必經之路。樂托在整個探險過程中亦是以一種強烈的樂觀精神貫穿始終。
不斷記錄繪制故事的莫尼則是想象界(he Imaginary)的具象。被繪制的毛伊與莫阿娜在海洋上的冒險故事正是第一部的基本劇情,這是經由莫阿娜(在冒險外)講述之后被留存下來的痕跡,也是一種對神話傳說的鏡像改寫。莫尼在羊皮紙上繪制的故事如同吟游詩人傳唱的史詩:
“敘事(narrative)既是探勘者(surveyor)的地理投射的結果,又是吟詠詩人(rhapsode)的作品。這個詞的詞源意義正是編織工(weaver)之意,因為編織工能將迥然相異的部分編織成一個整體。”[11]
莫尼也在羊皮紙故事中想象了自己與半神毛伊相遇后的歷程,并且得到了正主的認可。這是一種同人創作,一次文本盜獵,也是一次“神話的永恒回歸”。莫阿娜一行人去尋找被詛咒的島嶼莫圖斐度,亦是高度相似的“敘事盜獵”。看似這個冒險故事是僅此一次(hapax)的歷險,并且由于古神納羅全程并未出現,站在莫尼的視角完全可以認為對自然災害征服過程中的神話化事件改寫。而這份經歷同時也是對真正的波利尼西亞神話多次(pollakis)重演的替代互文性(intetextualité substitutive)延續。

《海洋奇緣2》海報:莫阿娜一行人與布滿繪圖線的大鯨魚
三、后海洋敘事的變化:從邊緣到中心
在莫尼的羊皮紙繪圖中所記錄的冒險與毛伊的神話文身和壁畫上的民族傳說相比,是一個具有后時性(ultériorité)的文本傳播,所形成的記憶(memorielle)差別正是對海洋敘事的一種抽象化認知。如果我們把“世界當做一個書海”,就會發現文本重復再創造形成了一個流動的家譜(généalogie),讓“被重復以及時間的流逝有了新的意義,使老作品不斷地進入新一輪意義的循環”[12],在這個過程中“中心”并不是作為被追尋的對象,而是文本在改頭換面(transfiguration)流變中的奇緣/起源。
筆者曾在《遨游神秘洋》專欄中詳細闡釋過“從陸地敘事到海洋敘事”的轉向,提到陸地敘事天然具備中心性,而海洋敘事則以游牧形態出現:
“陸地敘事有明確的目的地,無論是疆域的延展,還是新大陸的發現;陸地敘事的著重點亦不在旅途過程,出發點往往承擔鄉愁的功能。海洋敘事則更多是一種無目的流浪或冒險,不僅終點難以明確,甚至出發地都會被湮滅。……在海洋中游蕩,同時也意味著“大陸/中心”情結面臨挑戰。由于海洋本身的綿延性,導致領域既不可分,又無法確定中心,似乎唯一能確認的,就是正在航行中的船只。”[13]
不過在本作中,海洋敘事向著后設方向演變。被困在巨大蛤蜊中的蝙蝠女瑪丹姬(Matangi)所唱的《放手》(Get Lost)插曲里的“沒有地圖帶領你去終點,沒有答案解開你的疑問”則從天空敘事的視野,為莫阿娜一行人注入了與其他海洋敘事所不同的可能性,這便是后海洋敘事。
沉沒的莫圖斐度島嶼無疑是整個海洋得以重新聯結的“中心”,幾乎是作為神話核心的宇宙之軸(axis mundi)交匯點而存在。在傳統神話中,這樣的中心就是眾神之門(Bâb-ilâni),是“大洪水淹沒不到之處”。但在本作里卻早已墜入深淵(tehôm),其中固然有重寫薩摩亞族毛伊神話的緣故,但其神話學本質則是將整個敘事范式進行了翻轉[14]。所以直到它被重新勾出水面,都不是托馬斯·莫爾語境下的如同幸福彼岸一般的烏托邦島,而是一個如同圣壇模樣存在的雙峰格局,用以重新在實質層面建立起其他海洋民族發現彼此的紐帶。
在故事最后,雖然已經存在被重新升格為中心的莫圖斐度,但其他海洋民族并沒有將其當做真正的核位(the core),相反原本可能是存在于邊緣(the periphery)的莫圖魯尼島成為了重聚的空間。
這些海洋民族也變成再繪制地圖的解域化力量,解構了陸地/海洋、中心/邊緣、西方/東方、現實/想象、上位/下位的二元對立結構,以一種更加半邊緣(semiperiphery)的第三空間(Thirdspace),即真實并想象的(real-and-imagined)混合拓撲區域實現了空間轉向。
后海洋敘事的改寫也出現在不同角色的文身上。半神毛伊的文身講述的是他作為英雄拯救海洋的故事,他以嵌套自我的方式完成了海洋敘事下的經歷;而成為半神的莫阿娜,她的文身就不再是冒險,而是后海洋敘事下的更加流線化的紋路與莫圖斐度的紋樣結合。

《海洋奇緣2》海報:莫阿娜
《海洋奇緣2》在歐洲國家發行時,推出了包括夏威夷語、毛利語、大溪地語和薩摩亞語在內的四種波利尼西亞語言的特別配音版本。莫阿娜的名字Moana在毛利語和夏威夷語內都有大海的意思,在第二部結尾已經成為半神的她身上也擁有了類似海洋的地形草圖(sketch map),這既是身體的空間,也是空間的身體,每一處彎曲和流線都是身體紋路的一部分,也都是經歷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旅行隨行而知(knows as he goes)的知識與記憶的重現,“這一流動就像大地的輪廓,沿著一條路徑前行,具有各種之地的表面在視野里進出”[15]。于是貫穿著文身、記憶與敘事海洋冒險之旅不再是移動規整畫出平面的參考線(guidelines),而是自由流動中交互生成的繪圖線(plot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