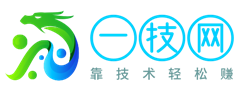央視2024年“世界糧食日”直播鏡頭里,重量不到3噸的紅色農(nóng)機在定西市魯家溝萬畝馬鈴薯高產(chǎn)示范項目種植基地的梯田間,在僅4米的半徑內(nèi)完成華麗轉身,還可實現(xiàn)20度田間坡道快速轉場和梯田高效作業(yè)。
這臺被全國馬鈴薯全程機械化專家組認定為國內(nèi)首臺丘陵山地四輪轉向馬鈴薯聯(lián)合收獲機,從研發(fā)到亮相,王虎存花費了整整四年時間。
王虎存正在組裝馬鈴薯聯(lián)合收獲機。本文圖片和視頻均由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馮寶強 攝制
王虎存,甘肅農(nóng)業(yè)大學在讀四年級博士研究生。從實驗室到田間地頭,從液壓油管到智能芯片,這位從平?jīng)錾綔侠镒叱龅?0后博士,帶著“讓農(nóng)民直起腰挖土豆”的樸素愿望,14年來,一直嘗試著用齒輪與智慧,在甘肅丘陵山地馬鈴薯收獲機械的研發(fā)上傾注心血,用青春在黃土地上書寫科技興農(nóng)的答卷。
甘肅丘陵山區(qū)地形復雜、馬鈴薯收獲機械化程度低。如今,這臺僅重2.95噸的“紅色精靈”,不僅能在梯田里“自由起舞”,更讓馬鈴薯畝收成本與簡易挖掘+人工撿拾收獲模式相比降低近150元,解決了丘陵山區(qū)馬鈴薯收獲無機可用、無好機可用的難題。
初心:黃土地里種下農(nóng)機夢
走進甘肅農(nóng)業(yè)大學機電工程學院的實驗車間,耳邊傳來機器歡快的轟鳴聲,這位戴著安全帽、身著普通工作服的農(nóng)機博士,正雙手沾滿機械油漬,操作激光數(shù)控切管機,對研發(fā)樣機的機架進行管料切割。墻角堆著十幾本有點泛黃的實驗記錄本,扉頁上工整寫著“馬鈴薯收獲機研發(fā)日志——王虎存”。
“每次翻開這些本子,都能想起第一次帶樣機下田的場景。”拿起其中一本還殘留著泥土的本子,王虎存感慨道。
王虎存正在記錄研發(fā)數(shù)據(jù)。
出生在平?jīng)鍪袥艽h一個小山村的王虎存,對土地有著天然的親近感。童年記憶里,父親在田里佝僂著腰挖土豆的背影,母親分揀土豆時粗糙的雙手,在他的心里烙下深深的印記。“那時我就經(jīng)常想能不能造臺機器讓他們直起腰來,盡可能地減少人力成本。”帶著這種夢想,2011年高考填報志愿時,王虎存不顧班主任勸阻,在第一志愿欄寫下“甘肅農(nóng)業(yè)大學農(nóng)業(yè)機械化及其自動化專業(yè)”。
“當時很多同學覺得學農(nóng)機沒前途,而且很苦。但我知道,在隴原大地,農(nóng)機就是改變農(nóng)民命運的‘鑰匙’。”王虎存說。
14年來,他連續(xù)攻讀甘肅農(nóng)業(yè)大學相關專業(yè)的碩士和博士,不斷學習農(nóng)業(yè)機械設計方面專業(yè)知識,并跟隨導師參與了多項西北旱區(qū)農(nóng)機裝備研發(fā)項目,尤其重點關注甘肅省丘陵山地馬鈴薯聯(lián)合收獲短板,依托甘肅省農(nóng)機裝備“一中心六基地”研發(fā)創(chuàng)新平臺,研究“小型化、輕量化、高效率、高質(zhì)量”的丘陵山地四輪轉向輪式馬鈴薯聯(lián)合收獲機,解決傳統(tǒng)馬鈴薯收獲作業(yè)勞動強度大、成本高、效率低的問題。
王虎存在學校實驗車間進行樣機軸類零件車削(車床操作)。
求學時,王虎存走得最多的路線就是從學校實驗加工車間到田間地頭。“我們在學校車間加工完試驗樣機,然后拉著樣機到田間地頭去試驗。這讓我積累了很多設備加工與田間試驗的科研經(jīng)驗。”王虎存介紹,導師趙武云教授的言傳身教更是他走上農(nóng)機研發(fā)這條路上最寶貴的財富。
王虎存說,導師會經(jīng)常帶他們?nèi)ヌ镩g地頭做試驗,導師近60歲的年紀依然和年輕人一起趴在農(nóng)機上調(diào)試設備。這種“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科研精神,同樣像一粒火種點燃著他的農(nóng)機夢。
匠心:與丘陵山地的較量
2023年秋,王虎存自主設計研發(fā)的第一代丘陵山地四輪轉向輪式馬鈴薯聯(lián)合收獲機問世。但在實際采收過程中,液壓系統(tǒng)漏油發(fā)熱、排膜裝置卡頓、駕駛員操作空間逼仄等問題,就像沉重的石頭壓在他的心頭。
首臺樣機失敗后,王虎存盯著田間冰冷的機器,內(nèi)心充滿了自責,責怪自己在技術方案上考慮不周。
“失敗是農(nóng)機人的必修課。人生哪有一次就成功的,我剛工作時,也出現(xiàn)過這種問題。別灰心,咱們從頭再來。”王虎存回憶那天趙武云老師拍著他的肩膀所說的這番話,再次讓他振作了起來。